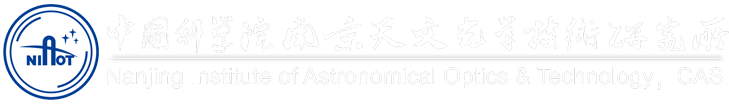苍生大医
庄仕华,武警新疆总队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入伍三十八年,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九次。二○○五年十一月获“中国医师奖”,二○○六年三月获“全国百姓放心医院院长”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新疆十大人物”,二○○七年五月被武警部队评为“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
有一年夏天,护士长于晓萍在庄仕华家里无意中看见了那些鞋。那些鞋摆放在贮藏室里,十七八双吧,胶鞋皮鞋,列着队。“你爸的吧?”于晓萍指着鞋说。那些鞋有个特征:鞋后帮通通卧倒,像统一做着一个规范的战术动作。庄岩告诉于晓萍,这些倒下的鞋帮呀,她一锤子一锤子一双一双地砸过。于晓萍与庄仕华在一块工作二十多年,知道院长平时穿鞋都趿拉着,进手术室出手术室,脱换时图个方便嘛。庄岩告诉她的于阿姨,不止这个。父亲每天做五六个小时的手术,每天查房三个多小时,全天基本是“站”和“走”,每天回到家,脚都是肿的,一摁一个坑。父亲的脚自然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正常地穿鞋,女儿就开始给父亲砸鞋帮,把硬扎扎的鞋帮砸倒、砸软,鞋帮软软的,父亲的脚就会舒服一些。
庄岩给父亲砸鞋帮,砸了很多年。她想,自己会一直砸下去吧,直到有一天父亲老了,挪不动腿了,兴许才会停止。
人际温度
五十四岁的帕依夏是个非常“专业”的患者,把自己的病早就研究透了。去年,她精心挑选了十月一日这天来到武警医院。她是个高敏患者,所有的西药都过敏,已经走了不少家医院。可是,胆石好取,过敏麻烦,哪家医院都不肯冒这个风险,武警医院是她最后的希望。她之所以选在十一长假来这儿动手术,就是考虑到节假日病人少,过敏源相对容易控制。即便这样,医生们也不愿意收下她,护理太难了,风险太大了,一旦手术中出现危急情况,抢救都无法进行。南方有一家大医院,因为病人对抗生素过敏导致死亡,被患者家属告上了法庭,结果给医院招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说句到底的话,武警医院没必要冒这个风险——也冒不起。医院的肝胆外科中心,眼下不仅在新疆、在全国有影响,甚至不少海外华侨也来看病。如果这个手术做砸了,就等于砸了自己的牌子。而庄仕华个人损失可能会更大——十万例手术,无一失败,难道要他亲手把自己这个惊人的纪录葬送吗?然而,大家都不同意收,庄仕华却坚持要收,说出的是一个不太着调的理由:“本来嘛,人长得挺漂亮的,因为对药物过敏,怕着凉感冒,一辈子连条裙子也不敢穿,多可怜啊;这又得了胆结石,够痛苦的了……”麻醉科主任再有两年就退休了,他正惦记着自己“安全着陆”的事,当时就跳了起来:“安全第一,我不干!”庄仕华板着脸说:“就你能干,你不干谁干!”
庄仕华给帕依夏做手术前,把能想到的准备都做了:没有病房,他让在四楼顶头腾出一个房间,那儿从来没有存放过药品,还调整了上下班通道。所有的工作服、病人用具全部更新,连病人的生活用品都按照他的要求买了新的。手术和术后恢复都很顺利,病人痊愈出院时,大家都很高兴,于晓萍朝大家伙眨着眼,逗庄仕华:“真可惜呀,治不了她的过敏症,这辈子她要是能穿上条裙子就好了。”
这种悬崖边上踩高跷的“悬事”,庄仕华干的可不止一件两件,这么多年,他手术过的特殊病人足有一百多号,年龄最大的一百零六岁,最小的才二十一个月。那个最小的病号叫杨怡菲,是阿克苏的一对夫妇从四川抱养的。孩子爱吃鸡蛋,可吃了之后又哭又闹。孩子好像不发育,自到了他们手里就没长过个儿,小脸黄黄的。他们想不要这个孩子了,可又有点儿舍不得。小龄结石,且先天性胆管畸形。这个“小龄结石”是收下了,可是,这么小的患者,麻醉根本无法保证,护理上更没有经验——这哪是什么“小龄结石”啊,分明就是庄院长捧回来的一颗“人体炸弹”。也就是庄院长,艺高、胆大、人好,连老天爷都在帮他,真就让他稳稳当当地“拆”了这颗“炸弹”,他生生从杨怡菲那粗不足零点三毫米的畸形胆管里,取出了半颗樱桃大的结石。住院期间,小女孩一看见庄仕华,就黏着他,像个小尾巴一样跟着他。
有人预言,飞速发展的医学,将导致现代医学分工日益细化,其后果使得过去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切换为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甚至几个医生同时面对一个病人。这样的发展无疑以牺牲温情为代价,当医生面对病人的时候,他们的眼中很容易将对象分割为系统、器官,试图通过纯粹的技术手段消灭病源。这种技术主义的逻辑无疑会导致一个基本事实的被忽视:医乃仁术。一个“仁”字,道出了医学的本体。说到底,医学是一种特殊的人际,而医生就是这种特殊人际的维护者,是人际温度的呈现者。通常,一个社会出了问题,一定是人与人的关系出了问题,人对人的态度出了问题。大医医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庄仕华的所作所为直奔主题,就是冲着当下社会酥松低温的人际去的,他以一种持续而耐久的高温维护并体现着一种中华民族古老而又崭新的人际。
还是庄仕华和赛福琴结婚的头几年,一天中午,赛福琴回家见房门没锁,以为庄仕华在家,推门就进,吓得“哇”的一声跑了出来。原来她家厨房里有两个陌生人,一个男的手里还拎着把菜刀。她被吓坏了。那两个人赶紧追出来,说他们是住院病人的家属,是庄医生给了他们钥匙,让他们来家里给病人做顿可口的饭菜。庄仕华对病人的好,那是真的好,好到家了。去年春节前,肝胆科来了个六十六岁的胆囊癌患者,名叫杨双喜。他在乌鲁木齐打工,快要过年了,老板给发了工资,他这才有钱给自己看病。手术后,病人不消化,什么药都不顶用。其实,最好的消化药就是他自己的胆汁,早晚各喝一次,每次五十毫升。庄仕华又哄又劝,病人总算同意喝自己的胆汁了。可是,病人肝功不好,从引流管接他的胆汁时,护士就戴着手套。庄仕华看见了,说:“他本来就不愿意喝,知道你们嫌脏,他还能喝吗?”说完,他就自己去给杨双喜接胆汁,然后换了新药碗去给他煮,煮好后端给他喝。庄仕华对病人的好,让旁人心生疑惑:这年头儿真有这样的人?哪个星球派来的“外援”吧?庄仕华肯定不是圣贤,那么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就没有做作之心、虚饰之态?可问题是,做秀有他这样做的吗?一个人,能把做秀做成他这样,坚持做到几十年不动摇、不走板、不变形,做到人心公道,做到天地正义,那么,这种“做秀”我们就只能将它定义为——做人。
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晚七点多,武警医院跑来一个小女孩,看见穿军装的就扑,抱住不放,又哭又喊:“我妈妈快死了,救救我妈妈吧!”小女孩阿丽瓦热的哭喊牵出一辆板车,板车上躺着的就是她“快死了”的妈妈古丽莎。下午,古丽莎从洗衣店下班回到家,正要给孩子做饭,突然嘴里往外冒绿水,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这是胆结石的老毛病又犯了。阿丽瓦热又哭又喊,邻居卖菜的汉族老太太听到动静跑过来,急慌慌地说快去武警医院,找庄仕华。
果然是来对了地方,找准了人。庄仕华查看病情后说:“准备手术!”古丽莎从手术室出来,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等她醒来,护士告诉她,庄仕华从她的体内取出了一个鸡蛋大的结石。幸亏抢救及时,不然胆囊破裂,可能她的命就没了。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古丽莎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她的日子过得惨淡,下了岗的丈夫酗酒,去年又丢下她和两个孩子离家出走了,她独自强撑着这个家,找了份洗衣店工作,靠每月三百元的工资和政府的低保艰难度日。一个胆囊手术最少也要两千六百元。现在,手术做了,人也快出院了,可是住院费还摸不到个钱毛毛,她快要愁死了。她找到庄仕华,想留在医院当杂工,来抵自己的住院费。庄仕华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家的情况我们都知道,看病的钱我们帮你解决,你就带着孩子安心回家吧,好好养病!”后来她听说,庄仕华带头捐钱,为她交了住院费。出院那天,庄仕华把古丽莎母女送回家。他和司机从车上抬下两袋面、一袋大米、一桶油,还雇了辆三轮车拉来了一吨煤。
阿丽瓦热要上学了。庄仕华买了新书包、文具盒和本子送给她,还把她送到学校,办了入学手续,交了学费。阿丽瓦热从一年级开始,每学期考出好成绩,就给庄仕华送一顶小花帽。她自己不会做,就向妈妈学着做,现在已经送了十三顶小花帽。二○一一年四月,庄仕华帮古丽莎一家申请上了政府的廉租房。他掏钱设计装修,为这个新家买了煤气灶、微波炉、沐浴器和电视机。他的妻子赛福琴亲自给挑了窗帘、挂毯和地毯。拿到新房钥匙那天,古丽莎的手颤抖得厉害——八号楼三单元三○四号,她看了一遍又一遍,念了一遍又一遍,知道她也能过上好日子了。
岁月燃情
还是二○○三年的事。木扎别克得了胆结石,可这个剽悍的哈萨克牧人惧怕开刀,所以原本一个手术可以解决的事,却让他耽搁下来。犯了病,拿药顶,家里的几十只羊就这么一只接一只地“顶”了药费,一直到只剩下五只母羊,“顶”不动了,也不敢再“顶”了,再“顶”家里就只剩下羊毛了。一天,他到武警医院看一个住院的亲戚,离去时,突然胆绞痛,痛得他捂着肚子蹲在医院门口。正好,庄仕华提着水管子给花坛里的花浇水,一眼看见了他。庄仕华忙叫人把木扎别克扶到了急诊科,一查,原来是一粒结石卡住了胆囊颈部。庄仕华劝木扎别克,如果采取消炎的保守治疗,还是除不了病根。木扎别克坚持着不开刀,不做手术,说没钱。庄仕华说:“保守治疗要住院,至少要住一个月,也不少花钱。”木扎别克见庄仕华说得实在,就跟他老婆商量了,决定做这个能“去根”的手术。可是,他手里确实没钱。木扎别克的老婆东挪西凑,只拿来了两千元,至少还差五百多元。庄仕华说:“先治病,后说钱。”庄仕华马上安排了木扎别克的手术,抽血、化验,一切准备妥当,四个小时之后,把他推上了手术台。木扎别克一再跟庄仕华表示,我缺钱你们都给做手术,我绝对不能欠医院的钱。临出院之前,他让老婆把那五只羊赶到了医院,说他已经“侦察”妥妥的了,医院里有一个清真食堂——一只不够两只,两只不够三只,杀了它们,给医院食堂,顶医疗费,反正就是不能欠医院的钱。庄仕华听木扎别克在那儿磨牙,不言语。当时医院正好维修营房,漆门窗,他顺手抓过一把刷子,在每只羊身上抹了一块黄油漆,吩咐把羊赶到医院小农场的羊群里。木扎别克出院了。那五只羊也要跟上他一块回家——医院压根就没打算把它们变成“医药费”。庄仕华让木扎别克把羊赶回去:“农民不能没地,牧民不能没羊。”木扎别克明白自己碰上了好人,他的羊也碰上了好人——羊儿们显然受到了款待,像串了趟阔亲戚,个个都被养得肥肥的,白白的。过了几个月,木扎别克揣着卖羊毛的钱来医院结算医药费,会计告诉他账已经结过了,他欠的六百多块钱是庄院长替他垫上的。听了这话,那么个大块头的汉子,当时就抹开了眼泪。三年后,这五只羊发展壮大到二十多只。这年过“八一”,木扎别克从他的羊群里挑了只肥的宰了,收拾干净,扛着到医院来慰问庄仕华。庄仕华赶紧让食堂给羊过秤。这羊真够肥的,五十斤,一斤羊肉九块钱,当时他就把六百块钱摁在了木扎别克手里。
这位哈萨克牧民是质朴的,用质朴的方式给自己办大事。庄仕华的回应也是质朴的,他相信木扎别克不会赖账。医生本来就是个质朴的职业,是人心对人心。草根出身的庄仕华无疑是质朴的。从根底上讲,他的成长环境比较劣质。因为贫寒,庄仕华成长得艰辛;同时也是因为贫寒,他生活得饱满而丰盈。上学时,他连每个学期一块五毛钱的学费都交不起,小学到高中的学费是国家减免的。从小学到初中,一个叫马华友和一个叫陈淑英的老师一直资助他。上高中时,学校在二十公里以外,他每周都要背上糙米或者红薯去求学。学校食堂每周收两毛五分钱的菜金,他交不起。班主任老师杨泽超为了能让庄仕华尝到荤腥,打听到哪天食堂有肉菜,就替他交上那一天的菜金。刚当兵时,一次骑马摔伤住院,与一个名叫吐拉西的维吾尔族汉子住在同一个病房。吐拉西的妻子再都汗给丈夫送饭时,有好吃的都要多带一份给庄仕华。这些点点滴滴的温暖,在年深日久的岁月里滋生繁育,不知不觉中成了庄仕华精神生命的某种基质。
得之滴水,报以涌泉,这种朴素的美质,如今早已经由他手里的那把出神入化的手术刀放大为天山大漠般的恢宏气势——大医仁心,温暖苍生。
乌拉孜家在大泉村是数得着的富裕户,有十头牛,三百多只羊。可是,他和他的老婆帕拉木汗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牛羊连同全家的幸福生活咕咚一声,掉进了井里——乌拉孜放牧时一脚踩空,掉进了二十多米深的废弃矿井。颅骨破裂,腰椎三处骨折,大腿断成三截,右臂骨折……这一天是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四日,一个黑色的日子。经过六天六夜的抢救,乌拉孜活过来了。乌拉孜在武警医院一住四个多月,家里的钱用光了,牛羊全卖了。乌拉孜闹着要出院,帕拉木汗天天哭,除了哭,她什么都不会了,只会去找庄仕华。几年前,庄仕华为她做过胆囊手术,她认为那是一个“太好的人”。庄仕华找了车,把乌拉孜送回家。回到家的乌拉孜只剩一条命,人是废掉了,躺在床上不能动。帕拉木汗照料丈夫的吃喝拉撒,还要顶门过日子,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真的掉进了黑咕隆咚的井里。这时,庄仕华来了,自行车上驮着一袋面、一壶油,身上的挎包里还带着一些药品和导尿管。
庄仕华说:“我会经常来的。”
经常是多长?乌拉孜没想过,帕拉木汗不敢想;庄仕华没想,他知道事不是想的,是做的。从这天起,庄仕华半个月来一次,为乌拉孜做康复治疗。刚出院那会,乌拉孜大小便失禁,一天换二三十块尿布。帕拉木汗一天到晚不停地洗啊洗。庄仕华看了心疼,买了一台雪花牌洗衣机搬过来。几年后,庄仕华又给她买了一台双缸洗衣机。
为了给乌拉孜增加营养,庄仕华牵来了一头奶牛:“挤奶给乌拉孜喝,让他快点儿站起来。”帕拉木汗心疼死这头牛了,冬天怕它挨冻,特意缝了件棉袍给牛穿上。庄仕华一见,笑了。
经常有多长?庄仕华从来没想过,帕拉木汗也从来没想过,她记,记录下了这份“经常”在日日月月年年岁岁中的无限延长──把庄仕华与她家有关的桩桩件件写在纸条上、药品包装盒上、烟盒上,甚至是从前的布票背面,记了一百多张。
二○○二年,乌拉孜竟然站起来了。
庄仕华没想到帕拉木汗会作这样的记录。于他而言,岁月无言,冷暖自知,一个人来到这世上,做你应该做的,做好,就足够了。作为一个医生,病人就是你的天,是你的一切。新疆是肝胆疾病的高发地区,庄仕华的眼睛早就瞄在了这里。
武警新疆总队医院肝胆外科的成立颇有戏剧性。那时,庄仕华是外一科医生,科里收治了一位女患者,她点名要庄仕华给自己做手术,可是科里没这个安排。这位女患者就拢了二十多人在院里闹,非让庄仕华做手术不可。
“庄仕华你有本事,有本事就出去单干。”──肝胆外科小组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成立的。他钦点了四个人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其中就有护士于晓萍。庄仕华对于晓萍的感觉好极了:人漂亮,干活麻利,刀子嘴,豆腐心,能砍能撂,收放有度,能挑头扛事的,日后当有大用。可于晓萍对庄仕华的感觉却是云里一脚雾里一腿,没个谱儿。于晓萍不想跟庄仕华走,在外一科多好啊,一个月奖金能发一百多,顶上一个月的工资了。她拿不定主意,回家跟丈夫王大河商量。她说:“我烦他,烦那个人,烦死了!不想去。”那些年,于晓萍挺烦庄仕华的,不光她烦,外一科哪个不烦?那人事儿特多,简直是医疗队伍里的一个“另类”。科里一般忙在上午,发药换药治疗,下午就清闲了,连主任都有时间与大家聚在护士站聊天。只有庄仕华例外,这样的场合他从来不参加,他在病房里转。一个医生管四个病房,他不,科里的病房他都管、都查,哪个病人吊瓶里的药液快输完了,该拔针了,见护士没及时到位,他就把人家喊来,还拉长了脸训人家。
一天中午,于晓萍缠胶布,把大块的胶布撕成条状,再一条一条在胶棒上缠好。眼瞅就要下班了,她急着回家,手指头飘了,胶布缠得里出外进,龇牙咧嘴。她人前脚进门,庄仕华的电话追屁股就到了,让她马上回来。
“我已经到家了。”
“到家也得回来──混账东西!”
庄仕华骂了她“混账东西”,事搞大了。别看那人笑眯眯的,天生一张菩萨脸,可那是在病人面前,换了地方凶得很,骂人的口头语就是“混账东西”。于晓萍不敢当“混账东西”,当即返回,午饭也不吃,把胶布重新缠过,缠好后仔细查验,直到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混账”之处,才长出了一口气。那之后,于晓萍的胶布总是缠得又好又快。可是,她还是烦那个人。好烦人噢,他管护士不算,还管到医生头上,竟然查别的医生病历,查出了毛病就跟人家说:“徐医生,十二床的病历你没写,少打场篮球,补上吧!”徐医生就跟他瞪眼睛:“你是主任吗?”他像没看见,也没听见,第二天照旧。不过,有一点好,这人是个劳动模范,有时连护士也不愿干的活儿,他都干。一九八八年有个烧伤病人住进外一科,是个年轻的回族司机,叫司江路。那时,于晓萍还是个兵,当配餐员,她还记得那个司江路长得挺帅,身长足有一米八八。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心情烦躁,谁进来他骂谁,什么难听他骂什么,随手抓到什么就朝你砸。当时,谁都不愿进司江路的病房,只有庄仕华除外。庄仕华喂他吃药吃饭,给他端屎端尿,给他擦洗身子。四个月后,司江路可以下床活动了,可是,他的双腿肌肉萎缩,不会走路了。庄仕华每天扶着他在走廊练走路。那情景让人看了好可怜,司江路的个子太高了,为了保持身体平衡,他的手就摁在庄仕华的头上,抓着庄仕华的头发。就这样,一个多月。司江路康复出院时,一把把庄仕华搂在怀里,低哑着嗓子说:“你这个哥我认定了。”
“他对病人那么好,跟他干不会错。”王大河就说了这一句。于晓萍不再犹豫,进了庄仕华的肝胆小组。
新年到了,肝胆小组接收了第一个病人:哈密机务段退休职工张忠祥。手术后,病人高烧不退,他们不敢大意,庄仕华昼夜守在病房里,跟病人睡在一块,夜里一次次为病人擦身降温。大家都挺自觉,庄仕华不走,谁都不走。那时候,于晓萍女儿刚满十个月。孩子喝不了牛奶,过敏,喝了之后满脸起泡,保姆怕她不放心,每天抱着孩子来让她看一眼。保姆不敢进病房,于晓萍不敢出病房,就从病房的窗户往外看,眼巴巴地看保姆抱着女儿,在操场上转啊转。整整十天,病人的高烧退下去了,大家终于获得了“解放”。张忠祥的儿子来接父亲出院时,当着大家的面掏出一千元钱塞到庄仕华手里。这个钱当然不能收。张忠祥的儿子说:“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你们出去好好吃顿饭。”听了他的话,于晓萍的眼泪差点儿流出来。那一刻,她在心里说,值了。
从四个人的肝胆小组起步,到后来的肝胆科、肝胆外科中心,一路走来,庄仕华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走出了一个巨大的阵势:十万多例胆囊手术,无一失败;患者送的一万多面锦旗,挤满了三层楼的楼道;新疆武警总队医院,成了乌鲁木齐市的一块招牌。现在,每天预约“庄一刀”手术的病人有一百多。
万物的尺度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叶儿壮守望着北疆……”这曲《小白杨》,出自新疆北部边境巴尔鲁克山脉的塔斯提边防连。二○一○年五月,庄仕华带医疗队到这儿巡诊,碰到了一件稀罕事。
那天,庄仕华用棉签给几个兵往脚丫子上涂抹脚气膏,见一个小兵站在门口,眼睛瞪得圆圆的,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看。别人都走了,他不走,还在门口那儿站着,一动不动。庄仕华说:“你哪儿不舒服啊?”小兵脸儿涨得红红的,竟然眼泪汪汪:“你……就是庄家老大?”
搞清楚了,这娃娃姓张,是庄仕华的“纯”老乡,家在四川简阳,就住在庄仕华的邻村。打记事起就听娘念叨“庄家老大”,一直把“庄家老大”念叨成了将军。这娃娃就想啊,当兵去,去“庄家老大”那里当兵。也是巧,那年正好新疆部队来简阳接兵,小张一头扎到了新疆。到了部队才知道,自己参加的是解放军,跟“庄家老大”的武警部队不是“一伙”的——那天,小张眼泪汪汪地说:“庄家老大是……这样的啊!”
那天,小张还说,当兵后,庄仕华的事听到了许多,于是,他盼望着能见上“庄家老大”。在这个乡村青年的心目中,“庄家老大”无疑是个标高,是他闯世界可供参照的一把标尺。今天他见到了庄仕华,把家乡人口口相传的“庄家老大”跟眼前掰着士兵脚丫子抹药膏的将军叠印在了一起,等于这把标尺已经竖在了自己的面前──噢,“庄家老大”就是这么干成了将军的。
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人是万物之灵,充分认识人的价值,才能对人心存崇敬,所思所想所做就会把人放在首位。身为尺,心为度,量别人,量自己,丈量世界,也丈量人生。如果说“庄家老大”是小张闯世界的“标尺”,那么,武警战士马辉则把庄仕华当做测量人间冷暖的晴雨表。
一九九○年初,武警新疆总队塔城支队战士马辉突然高烧不退,一个大小伙子,体重竟然下降到二十三公斤,他得的是一种基因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严重时会心衰致死。一晃,马辉在武警医院住了八个年头了。这八年里,马辉的手已经严重变形,关节粗大,十指弯曲,碰到有人要跟他握手,他就赶紧把手背到身后。平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如果没有必要,绝对不出门。一天,庄仕华到军人病房查房,看了马辉写的字,说:“你字写得这么好,手一定很巧。”这话让马辉突然间意识到了什么——庄院长说我的手巧,那我的手就一定很巧。那年头,医院流行用废弃的输液管编金鱼,马辉也试着编起来。他把红粉笔研磨成粉末,兑入开水,给输液管上色消毒,编出来的金鱼要姿有姿要色有色,军人病房的医生护士都收到了马辉编的小金鱼。
马辉给自己买了条裤子,见人就问:“我这条裤子好看不好看?”又配了件T恤,“这件衣服好看不好看?”马辉出门了。有人问:“马辉,打扮这么精神干什么去呀?”马辉朗然道:“我上街去!”
马辉三十六岁生日这天,庄仕华和几个院领导到军人病区为马辉过生日。庄仕华把切下来的第一块蛋糕递到马辉手里。马辉说:“小时候过生日,我妈都给我煮两个鸡蛋,我就知道自己又长一岁了。今天我又长了一岁,真不知说什么好,就是想哭……”庄仕华说:“我们都是你的家人,想哭就哭吧,不丢人!”庄仕华知道马辉的心病,安排他当上了军人病区的保管员,协助护士长工作。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彻底报废的人,登记物品、照顾危重病人,有空还为病友解闷,跟他们聊天,每天快乐地忙活着——生活在马辉眼里重新鲜花盛开,庄仕华给了他重拾美好的动力。
庄仕华是个爱美的人,办公室的抽屉里放着一面小镜子,偶尔会拉开拿出小镜子照上一照,细细地梳理一下头发。他很爱惜自己,烟不抽,酒不喝,辣椒不吃,吃饭时手边放一碗清水,遇到菜咸了,放在水中涮涮才入口。他喜欢完美,习惯让一个完美的自己面对世界,以自己的方式兢兢业业丝丝入扣地打造着一个完美的世界。他要让完美成为一种尺度,成为自己应对世界的标准,也要让完美成为这个世界挑剔自己、衡量自己的一把尺子。
作为医生,他追求完美,做了十万多例胆囊手术无一失败。作为院长,他建设完美,医院从过去十四个科室三百张床位,发展到四十五个科室八百张床位。他一直兼任主任的肝胆科,从最初的一间病房四张床位,发展到现在九十间病房三百张床位,成了新疆武警部队的肝胆外科中心。他最大限度地减少住院患者的开支,在药品、器械、设备、耗材的采购上严格实行公开招标,当场开标,从关键环节上堵住了价格过高的漏洞,使同厂、同名、同剂量的药品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他叫停了投资一千二百多万元的招待所,把招待所改成了军人病区,又投资一百万添置了医疗器械,更换了相关配套设施,建立了文化活动中心,病区和病房同时达到“三星级”宾馆标准。仅二○○八年以来,医院先后为住院官兵补贴医药费三千三百万。
人心的疆域
无疑,这是一间办公室。办公室的每个位置,所有的器具,甚至飘荡在空气中的每一粒灰尘,都结结实实地写着两个字:慌乱。通常办公室里必备的物品,大多以“散”或“堆”的方式,被随意地归置成一个生硬的局面。这儿,就连喜欢一粒一粒擦拭灰尘的小战士,恐怕也不必时常光顾了吧。
很显然,这里不被重用。办公室的主人是武警新疆总队医院院长庄仕华,他一般不待在这儿,对于自己的办公室,他俨然是个过客,在这里办公不假,可它的存在却更像一个点缀。
二○○六年四月十四日上午,庄仕华去参加一个穆斯林逝者的葬礼。
这天,庄仕华出现在乌鲁木齐五家渠穆斯林墓地。死者林作英,六十三岁。依照伊斯兰教丧葬习俗,非穆斯林不能参加葬礼。早在一年前,林作英已是胆囊癌晚期,庄仕华叮嘱她的儿女,先不要把实情告诉病人,否则不利于病人术后恢复。第三天,庄仕华亲自为林作英做了胆囊摘除手术。一个多月后,她出院了。这之后,林作英认准了庄仕华,身体不适,非让庄仕华给她看病。二○○五年三月,林作英胃炎发作要住院,她坚持要住肝胆外科。庄仕华破例批准她住进了肝胆外科病房。
二○○六年二月,林作英体内癌细胞扩散,全身水肿,第三次住进肝胆外科。庄仕华在家里熬了粥给她拎过来,抽空就来看她,还给她喂药。后来,林作英非要认庄仕华做她的干儿子。林作英临死之前,专门给儿女们留下话:一定要请庄院长参加自己的葬礼。
二○○八年五月十七日晚上,庄仕华在病房里试穿俞艳萍为他做的布鞋。
新疆奇台县西北湾乡菜园子三村五十五岁的农民俞艳萍,胆囊炎突然发作,家人把她紧急送往乌鲁木齐,跑了四家医院,都不收,因为俞艳萍同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慢性支气管炎,手术风险太大。来探病的亲友建议,送武警医院吧。当晚,俞艳萍被送到武警医院时,已处于轻度休克。正在查房的庄仕华赶到急诊科,决定立即实施胆囊切除手术。他通知心内、耳鼻喉和麻醉几个科的有关专家,马上论证手术风险和手术中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手术方案。次日凌晨,俞艳萍被推入手术室,二十分钟后,手术顺利完成。恢复治疗中,俞艳萍发现庄仕华总是趿拉鞋走路,就问护士。护士说,脚大鞋小呗,院长每天上午做二十多台手术,晚上还要查房,脚天天都是肿的。俞艳萍决定给庄仕华做一双合脚的布鞋。为了能拓下庄仕华的鞋样,她悄悄在地上洒了水,等庄仕华查房时踩上,留下脚印。做鞋时,她加大了两个鞋码。俞艳萍要出院了,庄仕华到病房来送她。俞艳萍从枕头底下抽出布鞋,不好意思地递给庄仕华:“岁数大了,手劲没以前大……你要是穿着合脚,我再给你做一双。”
二○一○年六月五日下午,庄仕华在乡村巡诊,途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庄院长,我想听听你的声音……”电话是七十五岁的维吾尔族老太太帕依夏木打来的。她得的是胆囊癌,住院时已经转移扩散。帕依夏木就愿听庄仕华说话,每当病情加重,总想听听他的声音。庄仕华二话不说,跳上车奔回医院,三十多公里的路途,一直与帕依夏木保持着通话。等他赶到病房时,帕依夏木感觉自己的病真的好了许多。帕依夏木又活了三个多月。家人讲,相信庄院长,是支撑她多活了三个月的精神支柱。
……
以时间论,庄仕华每天在办公室工作超不过两个小时,处理事务,他更喜欢在办公室以外的其他场所,比如病房。他不习惯坐,更喜欢走着或者站着就把事办了。站嘛,会比坐多一个高度。走嘛,比坐多出一块天地,都是他喜欢的境界。站和走,是挺立,是拓展,是一个医生的生命去向。无论是作为职业医生,还是一个普通人,庄仕华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然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疆域——世道人心。
在肝胆外科护士站的墙上,挂着一面特别的锦旗。这面锦旗是病人去世之后送来的,确切地说,是病人生前委托女儿在她去世后送来的。
二○○六年十二月,肝胆科收治了一个六十七岁的胆囊癌晚期病人,叫高仰珍。在她治疗的五十六天里,庄仕华每天早晚都过来问寒问暖,还在家里熬了汤拎过来。住院期间,高仰珍多次出现危急情况,不论白天黑夜,庄仕华都亲自组织抢救。
春节到了,高仰珍不能回家过年,庄仕华对于晓萍说:“给病人创造个过年的条件!”于晓萍很快就“创造”了院长说的“条件”:病房的顶棚挂起了拉花,门口贴上了对联,门上贴好了“福”字,买了两条花床单,换一条备一条。于晓萍自己给高仰珍买了一套棉睡衣,替她换上。除夕夜,庄仕华带来了糖果、卤货和馓子,科主任刘中齐带来了自己亲手做的红烧肉,他们陪着高仰珍,一块在她的“家”里看春晚。
高仰珍去世了。
病房里却没有哭声。于晓萍感到奇怪,推开门,见三个女儿都紧捂着嘴,在流泪。于晓萍忙说:“大声哭吧,哭出来会好受些。”她们还是没有大声哭出来。母亲的遗体被推到了太平间。三个女儿扑上去,放声大哭。大女儿对于晓萍说:“我们不想在病房里哭,怕让别人听见了,以为你们手术没做好,怕影响你们医院,怕影响庄院长。”
于晓萍一听,眼窝一热,眼前被泪水模糊成一片。她觉得跟着庄仕华这样的领导干工作,这辈子值了。
(文章来源:《解放军文艺》2011年第10期)
有一年夏天,护士长于晓萍在庄仕华家里无意中看见了那些鞋。那些鞋摆放在贮藏室里,十七八双吧,胶鞋皮鞋,列着队。“你爸的吧?”于晓萍指着鞋说。那些鞋有个特征:鞋后帮通通卧倒,像统一做着一个规范的战术动作。庄岩告诉于晓萍,这些倒下的鞋帮呀,她一锤子一锤子一双一双地砸过。于晓萍与庄仕华在一块工作二十多年,知道院长平时穿鞋都趿拉着,进手术室出手术室,脱换时图个方便嘛。庄岩告诉她的于阿姨,不止这个。父亲每天做五六个小时的手术,每天查房三个多小时,全天基本是“站”和“走”,每天回到家,脚都是肿的,一摁一个坑。父亲的脚自然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正常地穿鞋,女儿就开始给父亲砸鞋帮,把硬扎扎的鞋帮砸倒、砸软,鞋帮软软的,父亲的脚就会舒服一些。
庄岩给父亲砸鞋帮,砸了很多年。她想,自己会一直砸下去吧,直到有一天父亲老了,挪不动腿了,兴许才会停止。
人际温度
五十四岁的帕依夏是个非常“专业”的患者,把自己的病早就研究透了。去年,她精心挑选了十月一日这天来到武警医院。她是个高敏患者,所有的西药都过敏,已经走了不少家医院。可是,胆石好取,过敏麻烦,哪家医院都不肯冒这个风险,武警医院是她最后的希望。她之所以选在十一长假来这儿动手术,就是考虑到节假日病人少,过敏源相对容易控制。即便这样,医生们也不愿意收下她,护理太难了,风险太大了,一旦手术中出现危急情况,抢救都无法进行。南方有一家大医院,因为病人对抗生素过敏导致死亡,被患者家属告上了法庭,结果给医院招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说句到底的话,武警医院没必要冒这个风险——也冒不起。医院的肝胆外科中心,眼下不仅在新疆、在全国有影响,甚至不少海外华侨也来看病。如果这个手术做砸了,就等于砸了自己的牌子。而庄仕华个人损失可能会更大——十万例手术,无一失败,难道要他亲手把自己这个惊人的纪录葬送吗?然而,大家都不同意收,庄仕华却坚持要收,说出的是一个不太着调的理由:“本来嘛,人长得挺漂亮的,因为对药物过敏,怕着凉感冒,一辈子连条裙子也不敢穿,多可怜啊;这又得了胆结石,够痛苦的了……”麻醉科主任再有两年就退休了,他正惦记着自己“安全着陆”的事,当时就跳了起来:“安全第一,我不干!”庄仕华板着脸说:“就你能干,你不干谁干!”
庄仕华给帕依夏做手术前,把能想到的准备都做了:没有病房,他让在四楼顶头腾出一个房间,那儿从来没有存放过药品,还调整了上下班通道。所有的工作服、病人用具全部更新,连病人的生活用品都按照他的要求买了新的。手术和术后恢复都很顺利,病人痊愈出院时,大家都很高兴,于晓萍朝大家伙眨着眼,逗庄仕华:“真可惜呀,治不了她的过敏症,这辈子她要是能穿上条裙子就好了。”
这种悬崖边上踩高跷的“悬事”,庄仕华干的可不止一件两件,这么多年,他手术过的特殊病人足有一百多号,年龄最大的一百零六岁,最小的才二十一个月。那个最小的病号叫杨怡菲,是阿克苏的一对夫妇从四川抱养的。孩子爱吃鸡蛋,可吃了之后又哭又闹。孩子好像不发育,自到了他们手里就没长过个儿,小脸黄黄的。他们想不要这个孩子了,可又有点儿舍不得。小龄结石,且先天性胆管畸形。这个“小龄结石”是收下了,可是,这么小的患者,麻醉根本无法保证,护理上更没有经验——这哪是什么“小龄结石”啊,分明就是庄院长捧回来的一颗“人体炸弹”。也就是庄院长,艺高、胆大、人好,连老天爷都在帮他,真就让他稳稳当当地“拆”了这颗“炸弹”,他生生从杨怡菲那粗不足零点三毫米的畸形胆管里,取出了半颗樱桃大的结石。住院期间,小女孩一看见庄仕华,就黏着他,像个小尾巴一样跟着他。
有人预言,飞速发展的医学,将导致现代医学分工日益细化,其后果使得过去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切换为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甚至几个医生同时面对一个病人。这样的发展无疑以牺牲温情为代价,当医生面对病人的时候,他们的眼中很容易将对象分割为系统、器官,试图通过纯粹的技术手段消灭病源。这种技术主义的逻辑无疑会导致一个基本事实的被忽视:医乃仁术。一个“仁”字,道出了医学的本体。说到底,医学是一种特殊的人际,而医生就是这种特殊人际的维护者,是人际温度的呈现者。通常,一个社会出了问题,一定是人与人的关系出了问题,人对人的态度出了问题。大医医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庄仕华的所作所为直奔主题,就是冲着当下社会酥松低温的人际去的,他以一种持续而耐久的高温维护并体现着一种中华民族古老而又崭新的人际。
还是庄仕华和赛福琴结婚的头几年,一天中午,赛福琴回家见房门没锁,以为庄仕华在家,推门就进,吓得“哇”的一声跑了出来。原来她家厨房里有两个陌生人,一个男的手里还拎着把菜刀。她被吓坏了。那两个人赶紧追出来,说他们是住院病人的家属,是庄医生给了他们钥匙,让他们来家里给病人做顿可口的饭菜。庄仕华对病人的好,那是真的好,好到家了。去年春节前,肝胆科来了个六十六岁的胆囊癌患者,名叫杨双喜。他在乌鲁木齐打工,快要过年了,老板给发了工资,他这才有钱给自己看病。手术后,病人不消化,什么药都不顶用。其实,最好的消化药就是他自己的胆汁,早晚各喝一次,每次五十毫升。庄仕华又哄又劝,病人总算同意喝自己的胆汁了。可是,病人肝功不好,从引流管接他的胆汁时,护士就戴着手套。庄仕华看见了,说:“他本来就不愿意喝,知道你们嫌脏,他还能喝吗?”说完,他就自己去给杨双喜接胆汁,然后换了新药碗去给他煮,煮好后端给他喝。庄仕华对病人的好,让旁人心生疑惑:这年头儿真有这样的人?哪个星球派来的“外援”吧?庄仕华肯定不是圣贤,那么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就没有做作之心、虚饰之态?可问题是,做秀有他这样做的吗?一个人,能把做秀做成他这样,坚持做到几十年不动摇、不走板、不变形,做到人心公道,做到天地正义,那么,这种“做秀”我们就只能将它定义为——做人。
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晚七点多,武警医院跑来一个小女孩,看见穿军装的就扑,抱住不放,又哭又喊:“我妈妈快死了,救救我妈妈吧!”小女孩阿丽瓦热的哭喊牵出一辆板车,板车上躺着的就是她“快死了”的妈妈古丽莎。下午,古丽莎从洗衣店下班回到家,正要给孩子做饭,突然嘴里往外冒绿水,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这是胆结石的老毛病又犯了。阿丽瓦热又哭又喊,邻居卖菜的汉族老太太听到动静跑过来,急慌慌地说快去武警医院,找庄仕华。
果然是来对了地方,找准了人。庄仕华查看病情后说:“准备手术!”古丽莎从手术室出来,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等她醒来,护士告诉她,庄仕华从她的体内取出了一个鸡蛋大的结石。幸亏抢救及时,不然胆囊破裂,可能她的命就没了。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古丽莎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她的日子过得惨淡,下了岗的丈夫酗酒,去年又丢下她和两个孩子离家出走了,她独自强撑着这个家,找了份洗衣店工作,靠每月三百元的工资和政府的低保艰难度日。一个胆囊手术最少也要两千六百元。现在,手术做了,人也快出院了,可是住院费还摸不到个钱毛毛,她快要愁死了。她找到庄仕华,想留在医院当杂工,来抵自己的住院费。庄仕华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家的情况我们都知道,看病的钱我们帮你解决,你就带着孩子安心回家吧,好好养病!”后来她听说,庄仕华带头捐钱,为她交了住院费。出院那天,庄仕华把古丽莎母女送回家。他和司机从车上抬下两袋面、一袋大米、一桶油,还雇了辆三轮车拉来了一吨煤。
阿丽瓦热要上学了。庄仕华买了新书包、文具盒和本子送给她,还把她送到学校,办了入学手续,交了学费。阿丽瓦热从一年级开始,每学期考出好成绩,就给庄仕华送一顶小花帽。她自己不会做,就向妈妈学着做,现在已经送了十三顶小花帽。二○一一年四月,庄仕华帮古丽莎一家申请上了政府的廉租房。他掏钱设计装修,为这个新家买了煤气灶、微波炉、沐浴器和电视机。他的妻子赛福琴亲自给挑了窗帘、挂毯和地毯。拿到新房钥匙那天,古丽莎的手颤抖得厉害——八号楼三单元三○四号,她看了一遍又一遍,念了一遍又一遍,知道她也能过上好日子了。
岁月燃情
还是二○○三年的事。木扎别克得了胆结石,可这个剽悍的哈萨克牧人惧怕开刀,所以原本一个手术可以解决的事,却让他耽搁下来。犯了病,拿药顶,家里的几十只羊就这么一只接一只地“顶”了药费,一直到只剩下五只母羊,“顶”不动了,也不敢再“顶”了,再“顶”家里就只剩下羊毛了。一天,他到武警医院看一个住院的亲戚,离去时,突然胆绞痛,痛得他捂着肚子蹲在医院门口。正好,庄仕华提着水管子给花坛里的花浇水,一眼看见了他。庄仕华忙叫人把木扎别克扶到了急诊科,一查,原来是一粒结石卡住了胆囊颈部。庄仕华劝木扎别克,如果采取消炎的保守治疗,还是除不了病根。木扎别克坚持着不开刀,不做手术,说没钱。庄仕华说:“保守治疗要住院,至少要住一个月,也不少花钱。”木扎别克见庄仕华说得实在,就跟他老婆商量了,决定做这个能“去根”的手术。可是,他手里确实没钱。木扎别克的老婆东挪西凑,只拿来了两千元,至少还差五百多元。庄仕华说:“先治病,后说钱。”庄仕华马上安排了木扎别克的手术,抽血、化验,一切准备妥当,四个小时之后,把他推上了手术台。木扎别克一再跟庄仕华表示,我缺钱你们都给做手术,我绝对不能欠医院的钱。临出院之前,他让老婆把那五只羊赶到了医院,说他已经“侦察”妥妥的了,医院里有一个清真食堂——一只不够两只,两只不够三只,杀了它们,给医院食堂,顶医疗费,反正就是不能欠医院的钱。庄仕华听木扎别克在那儿磨牙,不言语。当时医院正好维修营房,漆门窗,他顺手抓过一把刷子,在每只羊身上抹了一块黄油漆,吩咐把羊赶到医院小农场的羊群里。木扎别克出院了。那五只羊也要跟上他一块回家——医院压根就没打算把它们变成“医药费”。庄仕华让木扎别克把羊赶回去:“农民不能没地,牧民不能没羊。”木扎别克明白自己碰上了好人,他的羊也碰上了好人——羊儿们显然受到了款待,像串了趟阔亲戚,个个都被养得肥肥的,白白的。过了几个月,木扎别克揣着卖羊毛的钱来医院结算医药费,会计告诉他账已经结过了,他欠的六百多块钱是庄院长替他垫上的。听了这话,那么个大块头的汉子,当时就抹开了眼泪。三年后,这五只羊发展壮大到二十多只。这年过“八一”,木扎别克从他的羊群里挑了只肥的宰了,收拾干净,扛着到医院来慰问庄仕华。庄仕华赶紧让食堂给羊过秤。这羊真够肥的,五十斤,一斤羊肉九块钱,当时他就把六百块钱摁在了木扎别克手里。
这位哈萨克牧民是质朴的,用质朴的方式给自己办大事。庄仕华的回应也是质朴的,他相信木扎别克不会赖账。医生本来就是个质朴的职业,是人心对人心。草根出身的庄仕华无疑是质朴的。从根底上讲,他的成长环境比较劣质。因为贫寒,庄仕华成长得艰辛;同时也是因为贫寒,他生活得饱满而丰盈。上学时,他连每个学期一块五毛钱的学费都交不起,小学到高中的学费是国家减免的。从小学到初中,一个叫马华友和一个叫陈淑英的老师一直资助他。上高中时,学校在二十公里以外,他每周都要背上糙米或者红薯去求学。学校食堂每周收两毛五分钱的菜金,他交不起。班主任老师杨泽超为了能让庄仕华尝到荤腥,打听到哪天食堂有肉菜,就替他交上那一天的菜金。刚当兵时,一次骑马摔伤住院,与一个名叫吐拉西的维吾尔族汉子住在同一个病房。吐拉西的妻子再都汗给丈夫送饭时,有好吃的都要多带一份给庄仕华。这些点点滴滴的温暖,在年深日久的岁月里滋生繁育,不知不觉中成了庄仕华精神生命的某种基质。
得之滴水,报以涌泉,这种朴素的美质,如今早已经由他手里的那把出神入化的手术刀放大为天山大漠般的恢宏气势——大医仁心,温暖苍生。
乌拉孜家在大泉村是数得着的富裕户,有十头牛,三百多只羊。可是,他和他的老婆帕拉木汗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牛羊连同全家的幸福生活咕咚一声,掉进了井里——乌拉孜放牧时一脚踩空,掉进了二十多米深的废弃矿井。颅骨破裂,腰椎三处骨折,大腿断成三截,右臂骨折……这一天是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四日,一个黑色的日子。经过六天六夜的抢救,乌拉孜活过来了。乌拉孜在武警医院一住四个多月,家里的钱用光了,牛羊全卖了。乌拉孜闹着要出院,帕拉木汗天天哭,除了哭,她什么都不会了,只会去找庄仕华。几年前,庄仕华为她做过胆囊手术,她认为那是一个“太好的人”。庄仕华找了车,把乌拉孜送回家。回到家的乌拉孜只剩一条命,人是废掉了,躺在床上不能动。帕拉木汗照料丈夫的吃喝拉撒,还要顶门过日子,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真的掉进了黑咕隆咚的井里。这时,庄仕华来了,自行车上驮着一袋面、一壶油,身上的挎包里还带着一些药品和导尿管。
庄仕华说:“我会经常来的。”
经常是多长?乌拉孜没想过,帕拉木汗不敢想;庄仕华没想,他知道事不是想的,是做的。从这天起,庄仕华半个月来一次,为乌拉孜做康复治疗。刚出院那会,乌拉孜大小便失禁,一天换二三十块尿布。帕拉木汗一天到晚不停地洗啊洗。庄仕华看了心疼,买了一台雪花牌洗衣机搬过来。几年后,庄仕华又给她买了一台双缸洗衣机。
为了给乌拉孜增加营养,庄仕华牵来了一头奶牛:“挤奶给乌拉孜喝,让他快点儿站起来。”帕拉木汗心疼死这头牛了,冬天怕它挨冻,特意缝了件棉袍给牛穿上。庄仕华一见,笑了。
经常有多长?庄仕华从来没想过,帕拉木汗也从来没想过,她记,记录下了这份“经常”在日日月月年年岁岁中的无限延长──把庄仕华与她家有关的桩桩件件写在纸条上、药品包装盒上、烟盒上,甚至是从前的布票背面,记了一百多张。
二○○二年,乌拉孜竟然站起来了。
庄仕华没想到帕拉木汗会作这样的记录。于他而言,岁月无言,冷暖自知,一个人来到这世上,做你应该做的,做好,就足够了。作为一个医生,病人就是你的天,是你的一切。新疆是肝胆疾病的高发地区,庄仕华的眼睛早就瞄在了这里。
武警新疆总队医院肝胆外科的成立颇有戏剧性。那时,庄仕华是外一科医生,科里收治了一位女患者,她点名要庄仕华给自己做手术,可是科里没这个安排。这位女患者就拢了二十多人在院里闹,非让庄仕华做手术不可。
“庄仕华你有本事,有本事就出去单干。”──肝胆外科小组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成立的。他钦点了四个人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其中就有护士于晓萍。庄仕华对于晓萍的感觉好极了:人漂亮,干活麻利,刀子嘴,豆腐心,能砍能撂,收放有度,能挑头扛事的,日后当有大用。可于晓萍对庄仕华的感觉却是云里一脚雾里一腿,没个谱儿。于晓萍不想跟庄仕华走,在外一科多好啊,一个月奖金能发一百多,顶上一个月的工资了。她拿不定主意,回家跟丈夫王大河商量。她说:“我烦他,烦那个人,烦死了!不想去。”那些年,于晓萍挺烦庄仕华的,不光她烦,外一科哪个不烦?那人事儿特多,简直是医疗队伍里的一个“另类”。科里一般忙在上午,发药换药治疗,下午就清闲了,连主任都有时间与大家聚在护士站聊天。只有庄仕华例外,这样的场合他从来不参加,他在病房里转。一个医生管四个病房,他不,科里的病房他都管、都查,哪个病人吊瓶里的药液快输完了,该拔针了,见护士没及时到位,他就把人家喊来,还拉长了脸训人家。
一天中午,于晓萍缠胶布,把大块的胶布撕成条状,再一条一条在胶棒上缠好。眼瞅就要下班了,她急着回家,手指头飘了,胶布缠得里出外进,龇牙咧嘴。她人前脚进门,庄仕华的电话追屁股就到了,让她马上回来。
“我已经到家了。”
“到家也得回来──混账东西!”
庄仕华骂了她“混账东西”,事搞大了。别看那人笑眯眯的,天生一张菩萨脸,可那是在病人面前,换了地方凶得很,骂人的口头语就是“混账东西”。于晓萍不敢当“混账东西”,当即返回,午饭也不吃,把胶布重新缠过,缠好后仔细查验,直到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混账”之处,才长出了一口气。那之后,于晓萍的胶布总是缠得又好又快。可是,她还是烦那个人。好烦人噢,他管护士不算,还管到医生头上,竟然查别的医生病历,查出了毛病就跟人家说:“徐医生,十二床的病历你没写,少打场篮球,补上吧!”徐医生就跟他瞪眼睛:“你是主任吗?”他像没看见,也没听见,第二天照旧。不过,有一点好,这人是个劳动模范,有时连护士也不愿干的活儿,他都干。一九八八年有个烧伤病人住进外一科,是个年轻的回族司机,叫司江路。那时,于晓萍还是个兵,当配餐员,她还记得那个司江路长得挺帅,身长足有一米八八。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心情烦躁,谁进来他骂谁,什么难听他骂什么,随手抓到什么就朝你砸。当时,谁都不愿进司江路的病房,只有庄仕华除外。庄仕华喂他吃药吃饭,给他端屎端尿,给他擦洗身子。四个月后,司江路可以下床活动了,可是,他的双腿肌肉萎缩,不会走路了。庄仕华每天扶着他在走廊练走路。那情景让人看了好可怜,司江路的个子太高了,为了保持身体平衡,他的手就摁在庄仕华的头上,抓着庄仕华的头发。就这样,一个多月。司江路康复出院时,一把把庄仕华搂在怀里,低哑着嗓子说:“你这个哥我认定了。”
“他对病人那么好,跟他干不会错。”王大河就说了这一句。于晓萍不再犹豫,进了庄仕华的肝胆小组。
新年到了,肝胆小组接收了第一个病人:哈密机务段退休职工张忠祥。手术后,病人高烧不退,他们不敢大意,庄仕华昼夜守在病房里,跟病人睡在一块,夜里一次次为病人擦身降温。大家都挺自觉,庄仕华不走,谁都不走。那时候,于晓萍女儿刚满十个月。孩子喝不了牛奶,过敏,喝了之后满脸起泡,保姆怕她不放心,每天抱着孩子来让她看一眼。保姆不敢进病房,于晓萍不敢出病房,就从病房的窗户往外看,眼巴巴地看保姆抱着女儿,在操场上转啊转。整整十天,病人的高烧退下去了,大家终于获得了“解放”。张忠祥的儿子来接父亲出院时,当着大家的面掏出一千元钱塞到庄仕华手里。这个钱当然不能收。张忠祥的儿子说:“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你们出去好好吃顿饭。”听了他的话,于晓萍的眼泪差点儿流出来。那一刻,她在心里说,值了。
从四个人的肝胆小组起步,到后来的肝胆科、肝胆外科中心,一路走来,庄仕华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走出了一个巨大的阵势:十万多例胆囊手术,无一失败;患者送的一万多面锦旗,挤满了三层楼的楼道;新疆武警总队医院,成了乌鲁木齐市的一块招牌。现在,每天预约“庄一刀”手术的病人有一百多。
万物的尺度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叶儿壮守望着北疆……”这曲《小白杨》,出自新疆北部边境巴尔鲁克山脉的塔斯提边防连。二○一○年五月,庄仕华带医疗队到这儿巡诊,碰到了一件稀罕事。
那天,庄仕华用棉签给几个兵往脚丫子上涂抹脚气膏,见一个小兵站在门口,眼睛瞪得圆圆的,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看。别人都走了,他不走,还在门口那儿站着,一动不动。庄仕华说:“你哪儿不舒服啊?”小兵脸儿涨得红红的,竟然眼泪汪汪:“你……就是庄家老大?”
搞清楚了,这娃娃姓张,是庄仕华的“纯”老乡,家在四川简阳,就住在庄仕华的邻村。打记事起就听娘念叨“庄家老大”,一直把“庄家老大”念叨成了将军。这娃娃就想啊,当兵去,去“庄家老大”那里当兵。也是巧,那年正好新疆部队来简阳接兵,小张一头扎到了新疆。到了部队才知道,自己参加的是解放军,跟“庄家老大”的武警部队不是“一伙”的——那天,小张眼泪汪汪地说:“庄家老大是……这样的啊!”
那天,小张还说,当兵后,庄仕华的事听到了许多,于是,他盼望着能见上“庄家老大”。在这个乡村青年的心目中,“庄家老大”无疑是个标高,是他闯世界可供参照的一把标尺。今天他见到了庄仕华,把家乡人口口相传的“庄家老大”跟眼前掰着士兵脚丫子抹药膏的将军叠印在了一起,等于这把标尺已经竖在了自己的面前──噢,“庄家老大”就是这么干成了将军的。
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人是万物之灵,充分认识人的价值,才能对人心存崇敬,所思所想所做就会把人放在首位。身为尺,心为度,量别人,量自己,丈量世界,也丈量人生。如果说“庄家老大”是小张闯世界的“标尺”,那么,武警战士马辉则把庄仕华当做测量人间冷暖的晴雨表。
一九九○年初,武警新疆总队塔城支队战士马辉突然高烧不退,一个大小伙子,体重竟然下降到二十三公斤,他得的是一种基因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严重时会心衰致死。一晃,马辉在武警医院住了八个年头了。这八年里,马辉的手已经严重变形,关节粗大,十指弯曲,碰到有人要跟他握手,他就赶紧把手背到身后。平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如果没有必要,绝对不出门。一天,庄仕华到军人病房查房,看了马辉写的字,说:“你字写得这么好,手一定很巧。”这话让马辉突然间意识到了什么——庄院长说我的手巧,那我的手就一定很巧。那年头,医院流行用废弃的输液管编金鱼,马辉也试着编起来。他把红粉笔研磨成粉末,兑入开水,给输液管上色消毒,编出来的金鱼要姿有姿要色有色,军人病房的医生护士都收到了马辉编的小金鱼。
马辉给自己买了条裤子,见人就问:“我这条裤子好看不好看?”又配了件T恤,“这件衣服好看不好看?”马辉出门了。有人问:“马辉,打扮这么精神干什么去呀?”马辉朗然道:“我上街去!”
马辉三十六岁生日这天,庄仕华和几个院领导到军人病区为马辉过生日。庄仕华把切下来的第一块蛋糕递到马辉手里。马辉说:“小时候过生日,我妈都给我煮两个鸡蛋,我就知道自己又长一岁了。今天我又长了一岁,真不知说什么好,就是想哭……”庄仕华说:“我们都是你的家人,想哭就哭吧,不丢人!”庄仕华知道马辉的心病,安排他当上了军人病区的保管员,协助护士长工作。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彻底报废的人,登记物品、照顾危重病人,有空还为病友解闷,跟他们聊天,每天快乐地忙活着——生活在马辉眼里重新鲜花盛开,庄仕华给了他重拾美好的动力。
庄仕华是个爱美的人,办公室的抽屉里放着一面小镜子,偶尔会拉开拿出小镜子照上一照,细细地梳理一下头发。他很爱惜自己,烟不抽,酒不喝,辣椒不吃,吃饭时手边放一碗清水,遇到菜咸了,放在水中涮涮才入口。他喜欢完美,习惯让一个完美的自己面对世界,以自己的方式兢兢业业丝丝入扣地打造着一个完美的世界。他要让完美成为一种尺度,成为自己应对世界的标准,也要让完美成为这个世界挑剔自己、衡量自己的一把尺子。
作为医生,他追求完美,做了十万多例胆囊手术无一失败。作为院长,他建设完美,医院从过去十四个科室三百张床位,发展到四十五个科室八百张床位。他一直兼任主任的肝胆科,从最初的一间病房四张床位,发展到现在九十间病房三百张床位,成了新疆武警部队的肝胆外科中心。他最大限度地减少住院患者的开支,在药品、器械、设备、耗材的采购上严格实行公开招标,当场开标,从关键环节上堵住了价格过高的漏洞,使同厂、同名、同剂量的药品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他叫停了投资一千二百多万元的招待所,把招待所改成了军人病区,又投资一百万添置了医疗器械,更换了相关配套设施,建立了文化活动中心,病区和病房同时达到“三星级”宾馆标准。仅二○○八年以来,医院先后为住院官兵补贴医药费三千三百万。
人心的疆域
无疑,这是一间办公室。办公室的每个位置,所有的器具,甚至飘荡在空气中的每一粒灰尘,都结结实实地写着两个字:慌乱。通常办公室里必备的物品,大多以“散”或“堆”的方式,被随意地归置成一个生硬的局面。这儿,就连喜欢一粒一粒擦拭灰尘的小战士,恐怕也不必时常光顾了吧。
很显然,这里不被重用。办公室的主人是武警新疆总队医院院长庄仕华,他一般不待在这儿,对于自己的办公室,他俨然是个过客,在这里办公不假,可它的存在却更像一个点缀。
二○○六年四月十四日上午,庄仕华去参加一个穆斯林逝者的葬礼。
这天,庄仕华出现在乌鲁木齐五家渠穆斯林墓地。死者林作英,六十三岁。依照伊斯兰教丧葬习俗,非穆斯林不能参加葬礼。早在一年前,林作英已是胆囊癌晚期,庄仕华叮嘱她的儿女,先不要把实情告诉病人,否则不利于病人术后恢复。第三天,庄仕华亲自为林作英做了胆囊摘除手术。一个多月后,她出院了。这之后,林作英认准了庄仕华,身体不适,非让庄仕华给她看病。二○○五年三月,林作英胃炎发作要住院,她坚持要住肝胆外科。庄仕华破例批准她住进了肝胆外科病房。
二○○六年二月,林作英体内癌细胞扩散,全身水肿,第三次住进肝胆外科。庄仕华在家里熬了粥给她拎过来,抽空就来看她,还给她喂药。后来,林作英非要认庄仕华做她的干儿子。林作英临死之前,专门给儿女们留下话:一定要请庄院长参加自己的葬礼。
二○○八年五月十七日晚上,庄仕华在病房里试穿俞艳萍为他做的布鞋。
新疆奇台县西北湾乡菜园子三村五十五岁的农民俞艳萍,胆囊炎突然发作,家人把她紧急送往乌鲁木齐,跑了四家医院,都不收,因为俞艳萍同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慢性支气管炎,手术风险太大。来探病的亲友建议,送武警医院吧。当晚,俞艳萍被送到武警医院时,已处于轻度休克。正在查房的庄仕华赶到急诊科,决定立即实施胆囊切除手术。他通知心内、耳鼻喉和麻醉几个科的有关专家,马上论证手术风险和手术中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手术方案。次日凌晨,俞艳萍被推入手术室,二十分钟后,手术顺利完成。恢复治疗中,俞艳萍发现庄仕华总是趿拉鞋走路,就问护士。护士说,脚大鞋小呗,院长每天上午做二十多台手术,晚上还要查房,脚天天都是肿的。俞艳萍决定给庄仕华做一双合脚的布鞋。为了能拓下庄仕华的鞋样,她悄悄在地上洒了水,等庄仕华查房时踩上,留下脚印。做鞋时,她加大了两个鞋码。俞艳萍要出院了,庄仕华到病房来送她。俞艳萍从枕头底下抽出布鞋,不好意思地递给庄仕华:“岁数大了,手劲没以前大……你要是穿着合脚,我再给你做一双。”
二○一○年六月五日下午,庄仕华在乡村巡诊,途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庄院长,我想听听你的声音……”电话是七十五岁的维吾尔族老太太帕依夏木打来的。她得的是胆囊癌,住院时已经转移扩散。帕依夏木就愿听庄仕华说话,每当病情加重,总想听听他的声音。庄仕华二话不说,跳上车奔回医院,三十多公里的路途,一直与帕依夏木保持着通话。等他赶到病房时,帕依夏木感觉自己的病真的好了许多。帕依夏木又活了三个多月。家人讲,相信庄院长,是支撑她多活了三个月的精神支柱。
……
以时间论,庄仕华每天在办公室工作超不过两个小时,处理事务,他更喜欢在办公室以外的其他场所,比如病房。他不习惯坐,更喜欢走着或者站着就把事办了。站嘛,会比坐多一个高度。走嘛,比坐多出一块天地,都是他喜欢的境界。站和走,是挺立,是拓展,是一个医生的生命去向。无论是作为职业医生,还是一个普通人,庄仕华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然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疆域——世道人心。
在肝胆外科护士站的墙上,挂着一面特别的锦旗。这面锦旗是病人去世之后送来的,确切地说,是病人生前委托女儿在她去世后送来的。
二○○六年十二月,肝胆科收治了一个六十七岁的胆囊癌晚期病人,叫高仰珍。在她治疗的五十六天里,庄仕华每天早晚都过来问寒问暖,还在家里熬了汤拎过来。住院期间,高仰珍多次出现危急情况,不论白天黑夜,庄仕华都亲自组织抢救。
春节到了,高仰珍不能回家过年,庄仕华对于晓萍说:“给病人创造个过年的条件!”于晓萍很快就“创造”了院长说的“条件”:病房的顶棚挂起了拉花,门口贴上了对联,门上贴好了“福”字,买了两条花床单,换一条备一条。于晓萍自己给高仰珍买了一套棉睡衣,替她换上。除夕夜,庄仕华带来了糖果、卤货和馓子,科主任刘中齐带来了自己亲手做的红烧肉,他们陪着高仰珍,一块在她的“家”里看春晚。
高仰珍去世了。
病房里却没有哭声。于晓萍感到奇怪,推开门,见三个女儿都紧捂着嘴,在流泪。于晓萍忙说:“大声哭吧,哭出来会好受些。”她们还是没有大声哭出来。母亲的遗体被推到了太平间。三个女儿扑上去,放声大哭。大女儿对于晓萍说:“我们不想在病房里哭,怕让别人听见了,以为你们手术没做好,怕影响你们医院,怕影响庄院长。”
于晓萍一听,眼窝一热,眼前被泪水模糊成一片。她觉得跟着庄仕华这样的领导干工作,这辈子值了。
(文章来源:《解放军文艺》2011年第10期)